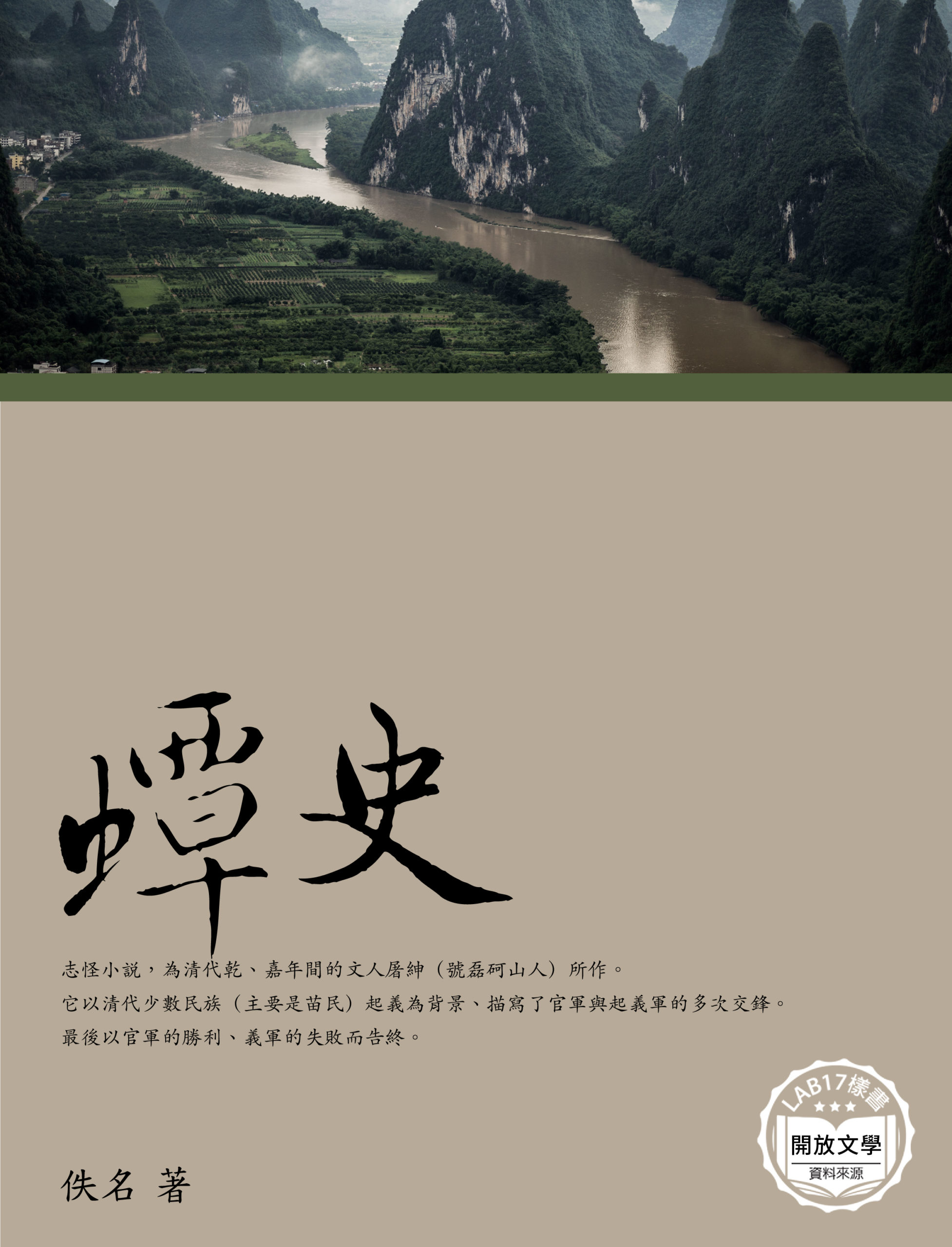蟫史
蟫史,志怪小説,為清代乾、嘉年間的文人屠紳所作。它以清代少數民族起義為背景、描寫了官軍與起義軍的多次交鋒。最後以官軍的勝利、義軍的失敗而告終。在戰爭場面的描寫中,作者吸收了神魔小説鬥法鬥寶的寫法,雖文字古奧,卻帶有神奇的色彩。
作品以清代中葉社會為背景,敍寫甘鼎、桑蜎等為首的官兵在諸異人的襄助下,先後平定了廣州王汴天化、交人屈蠔,五苗、川陝五斗教以及交址馗形等叛亂。其主要傾向是歪曲、誣衊兄弟民族和起義羣眾,歌頌為王前驅、功成身退的理想人物,鞏固封建統治。但也多少批判了當時的腐敗政治和黑暗官場。小説情節離奇,人物怪誕,文彩華豔而平板艱澀,是文言長篇小説的代表作之一。全書共寫了二百三十餘個人物,性格較鮮明者有甘鼎、桑蜎、婁萬赤等人。
書敍閩人桑蠋生出海落水,漂到甲子石外的海邊,被人救起,引見指揮使甘鼎,遂入其幕。甘鼎根據桑蠋生所提供的圖紙築成神奇城垣,二人又掘地得三篋天書,時時參看。石灣村鄺天龍作亂,桑佐甘鼎剿敵,又有龍女、矮腳道人來助,鄺天龍遭擒,甘鼎因功升鎮撫。
隴西公被圍,甘鼎往救,得天女木蘭相助。又遇員夫人,教以策略,聘高人司馬季孫及明化醇為參謀,掃蕩酉陽亂苗。又攻剿西南諸苗,仗木蘭以法術破敵,擒紅苗噩青氣。斬顯教島城的梅賊。甘鼎又奉命支援豫州石中丞,訪善幻術的都毛子,請其施術大破賊兵。又歷平黃苗,平定交恥,立交陸行省。甘鼎功成身退,棄官歸,桑蠋生也衣錦還鄉。
書中,作者從統治階級的立場出發,為鎮壓農民起義的統治者唱讚歌,醜化和貶斥兄弟民族與起義羣眾。把少數民族寫成不開化的野蠻人,讓他們變成牛鬼蛇神,一會兒以人形出現,一會兒又變成野獸。作者把起義首領寫成令人可怖的妖魔鬼怪,雖然逞兇一時,但一個個都逃脱不了覆滅的命運。作者自己多年在雲南、廣西一帶做官,本就是清王朝鎮壓少數民族和勞動人民的幫兇。書中主人公之一的桑蠋生就是作者的自況。桑蠋生説“予甲子生也”正是屠紳生年;書中的某些情節也與作者經歷基本一致。《蟫史》開篇所云“在昔吳儂官於粵嶺,行年大行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輒就見聞傳聞之異辭,匯為一編”。這也説明了《蜱史》的情節與作者的經歷的關係。全書的情節主幹——甘鼎平苗故事,更是明顯地影射乾隆六十年“傅鼎扦苗”之事。
小説總是通過主要人物的活動來體現其思想性的。《蟫史》的第一主人公甘鼎實際上就是清朝乾隆時期殘酷鎮壓西南苗族人民起義的大劊子手傅鼎的化身。甘鼎在《蟫史》中是個忠君衞道、竭力維護封建統治的“國之棟樑”人物。但就這個人物本身而言,由於作者沒有作個性化的刻畫、描寫,只見事不見“人”,所以形象並不鮮明。實際上,甘鼎只是作者藉以表達自己維護封建統治的觀念的工具。這種觀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因為甘鼎是統治階級的衞道者,所以他能得到眾多才智之士的擁戴和鼎助。作者自況的桑蠋生是跟隨甘鼎“建功立業”的股肱,建甲子城,得天書,平鄺天龍以至平諸苗,都離不開桑蠋生的出謀畫策之功。甘鼎所以能“屢建奇功”,正是依仗了桑蠋生、司馬季孫、明化諄這此“足智多謀”的軍師的籌畫。其二,因為甘鼎是封建統治秩序的維護者,所謂“替天行道”的代表,所以他能得到“神助”。
從藝術性來説,《蟫史》的主要特色是情節曲折多變,頗為引人入勝。書中人神互出,“正”“邪”雙方鬥智、鬥力、鬥法,想象力非常豐富,很有浪漫主義色彩。這無疑對於一般讀者來説是頗具吸引力的。《蟫史》能較為廣泛流傳,這是主要原因。
本書的表現手法,可以歸結為“幻”和“誕”兩個字。
書前“社陵男子序”認為作者寫《蟫史》的目的就是追求“幻”和“誕”。所謂“幻”就是虛構,“有可為無,無可為有”,通過“幻”達到“窮物之變”,就顯出“誕”。“誕”就是“怪怪奇奇,形形色色。”並且得出結論,認為“幻”和“誕”就使《蟫史》“聳人之聞”,以“饜好奇之心而供多聞之助”,其實,這只是見表不見裏的説法。從《蟫史》“幻”“誕”這一表面特點來看,似乎與“據史實之實錄”是不相干的,其實卻不然。
倒是《蟫史》小停道人序説得比較中肯。該序認為《蟫史》是“驅牛鬼蛇神與實錄中”,達到“於世道人心之一助”的目的。這就點出了《蟫史》的表現手法雖然是“幻”“誕”的,但作者的目的是影射歷史——歌頌傅鼎扦苗。在《蟫史》第二回有這樣一句話“怪怪奇奇書不盡啊,看予攬轡志澄清”。作者所謂的“志澄清”實際上就是鎮壓人民起義。所以説造成《蟫史》歪曲反映現實的不是“幻”和“誕”的浪漫主義表現手法而是作者的政治立場。另外,從《蟫史》的語言來看,由於作者有意賣弄文才,“勉造硬語,力擬古書”,讀起來令人感到艱澀生硬,詰屈聱牙。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相同方式分享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以及修改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若使用者修改該著作時,僅得依本授權條款或與本授權條款類似者來散布該衍生作品。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您可自由:
分享 —
以任何媒介或格式重製及散布本素材
修改 —
重混、轉換本素材、及依本素材建立新素材
只要您遵守授權條款規定,Lab17 電子書服務(包含 Lab17 電子書店及相關服務網站,以下簡稱「本服務」)不能撤回您使用本素材的自由。
姓名標示 —
您必須給予適當表彰、提供指向本授權條款的連結,以及指出(本作品的原始版本)是否已被變更。您可以任何合理方式為前述表彰,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授權人為您或您的使用方式背書。
非商業性 —
您不得將本素材進行商業目的之使用。
相同方式分享 —
若您重混、轉換本素材,或依本素材建立新素材,您必須依本素材的授權條款來散布你的貢獻物。
不得增加額外限制 —
您不能增設法律條款或科技措施,來限制別人依授權條款本已許可的作為。
聲明
當您使用本服務中屬於公眾領域的元素,或當法律有例外或限制條款允許您的使用,則您不需要遵守本授權條款。
未提供保證。本授權條款未必能完全提供,您預期用途所需要的所有許可。例如:形象權,隱私權、著作人格權等其他權利,可能限制您如何使用本素材。
相關商品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