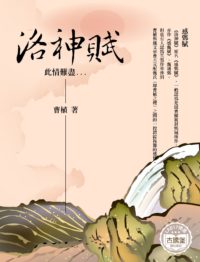這部譴責小説反映的,主要是晚清時期湖南、兩廣和福建等地區官場的黑暗現實。其中既有為了鑽營候補、不惜敗壞倫常道德的欺詐行為,也有買通關節、貪贓枉法的鬼蜮伎倆;既有明爭暗鬥、爾虞我詐的奸計暗謀,也有迷信卜乩、置千里赤地和百姓生計於不顧的昏憒顢頇;既有遭逢民變、聞風喪膽的各種醜態,又有科場應試、千奇百怪的眾生癭相。作者的筆觸上至省州台撫,下及裁縫、媒婆、堂館,活畫出一幅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社會圖景,而這種糊塗渾噩的現狀,無不導源於吏治的混亂和官場的腐敗。
因此,作為全書的一個總綱,書中第十回“老史著書官場盡相”一段,寫得最為精彩。其作用不亞於《紅樓夢》中的“護官符”。作者在這裏借“四川省裏第一個猾吏”楊鄂在湖北會館門生為他餞行時説的一番話,鞭辟入裏地總結了一個《升發須知》。他的這篇宏論被志在專鑽的惡吏奉為升官發財的至寶。《須知》的核心則在於“走上司的心經”,它包括如何看上司的人頭,怎樣巧妙地投其所好,先認清紅黑二字,再用錢鋪路通關。而其施用範圍除了上司本人外,還應當把他的紅人、心腹等周圍的人包括在外。所謂“現任的應酬,憲幕是第一義,巴結紳士是第二義”,即對洋人傳教士和地方百姓,也要敷衍和留心。尤其精闢的是,楊鄂還為他的這一套心機編了幾個字的訣竅:
曰紅,曰圓融,曰路路通,曰能辨骨董,曰不怕大虧空,曰麻雀牌九中中,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
有了這些訣竅,再加上隨機應變、靈活運用,就能混跡官場,長盛不衰,升發不愁。這一議論無疑是對當時官場現狀的高度概括,具有警時省世的作用。
就小説的寫作手法而言,作者採用的純是寫真紀事。他把自己在當時官場的所見所聞,如實地記載下來,並用《儒林外史》的構篇方式,把它們由人及事地聯貫下來。雖然沒有一些貫穿始終的主要人物,一種前呼後應的故事情節,但是事隨人生、人由事見的散式結構,卻如一個展開的橫段面,再現出清末社會的一片渾噩,其揭露和譴責的主題是很明顯的。
當然,作為報章的連載小説,它在總體結構上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加上十九回和十二回的區別,也使人難窺它的全貌,這是本書的一個缺憾,也是它未能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同樣引人注目的原因所在。
最後要論及的是它的題目。正如茂苑惜秋生在《序》中所言,在中國古代,以糊塗教人與教己者不乏其人。從屈原的《漁父》到鄭板橋的“難得糊塗”,無不藴含着一份對社會和對人生的清醒。作者以“糊塗世界”為名,很可以使人深感其中的批判意義,而這也正是作者在寫人記事的筆法中自寓褒貶的一種點露。它能使我們在讀這部小説時觀其事而知其意,取得一種温故而知新的警示效應。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相同方式分享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以及修改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若使用者修改該著作時,僅得依本授權條款或與本授權條款類似者來散布該衍生作品。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您可自由:
分享 —
以任何媒介或格式重製及散布本素材
修改 —
重混、轉換本素材、及依本素材建立新素材
只要您遵守授權條款規定,Lab17 電子書服務(包含 Lab17 電子書店及相關服務網站,以下簡稱「本服務」)不能撤回您使用本素材的自由。
姓名標示 —
您必須給予適當表彰、提供指向本授權條款的連結,以及指出(本作品的原始版本)是否已被變更。您可以任何合理方式為前述表彰,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授權人為您或您的使用方式背書。
非商業性 —
您不得將本素材進行商業目的之使用。
相同方式分享 —
若您重混、轉換本素材,或依本素材建立新素材,您必須依本素材的授權條款來散布你的貢獻物。
不得增加額外限制 —
您不能增設法律條款或科技措施,來限制別人依授權條款本已許可的作為。
聲明
當您使用本服務中屬於公眾領域的元素,或當法律有例外或限制條款允許您的使用,則您不需要遵守本授權條款。
未提供保證。本授權條款未必能完全提供,您預期用途所需要的所有許可。例如:形象權,隱私權、著作人格權等其他權利,可能限制您如何使用本素材。
相關商品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
語言文學